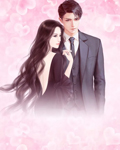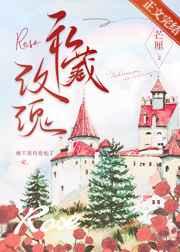第十四章 西部人的西部精神(2)
格林文学【glxsw.cc】第一时间更新《藏獒的精神》最新章节。
五
如果说自然的背景是从近到远无边深邃的天空,文化的背景就是从远到近无比璀璨的阳光。在寒冷的冬天触摸温暖的阳光,你会觉得世界的全部美好都在那一片阳光中停留。在西部的大地上感觉斑斓的文化,你会觉得它永远不可能是一件已成古董的器皿、一卷朱笔写成的残书、一座洞开于世的陵墓、一片雕梁画栋的建筑;而是活生生的场景一天又一天的日子,是阳光的高地、麦香扑鼻的庄稼后面正在进行的祈祷,是阴郁的山上嘎嘎鸣叫的鹰群之前经声大作的葬礼,是定居点的碉房三巷九陌之间铮铮琮琮的佩饰、七彩招摇的袍影和闪烁宝石的发辫,是赛马场上的奔跑、雪顿节的狂欢、松潘茶的苦香、打青稞的歌谣,是维吾尔族的“麦西热甫”(歌舞晚会)、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英雄史诗)、蒙古族的祭敖包、锡伯族的“喜利妈妈”(保佑家庭人口兴旺平安的神)、塔吉克族的肉孜节、回族的拉面、东乡族的花儿、哈萨克族的“吐马克”(高顶皮帽)、乌孜别克族的“科格乃”(音色优美的琴),等等,等等,不胜枚举。尽管我在前面已经声明,我是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的,此文中所谈的“西部人”以汉族为主,别的民族我将另文专论,但一谈到西部文化对“西部人”之形成的作用,就怎么也绕不开了,绕到哪里都是它们的存在。因为对一个人群来说,文化不仅仅是悬挂在他们身后的背景,更是他们可以纵深行走的前景;不仅仅是如影随形的伴侣,更是白昼的亮光、晚间的夜色、嘴边的空气、耳畔的声音,甚至就是他自己。是的,文化就是他自己。
每一个作为移民的西部人都曾经面对一个与自家传统迥然有异的生活空间。这个空间不管你爱不爱它,它都会以强大的力量拥抱你,直到你浑身放松稀里糊涂不知不觉成为它的人。春风风人,夏雨雨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就是对你的改造,是多种文化在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身上碰撞碎裂后的新一轮整合。它可能出现在你和你的后代身上,更可能出现在你的父辈或者祖辈身上,假如你的父辈祖辈早就来到了西部的话。但不管这样的整合出现在谁的身上,它都是不声不响不留形迹的。潜移默化,自然似之,永远是它作用于人的唯一方式。
更重要的是,在移民的生活空间里,本土文化的出现也就是本土居民的出现。本土的居民微笑着朝你走来,带着热情和温暖站在了你的眼前身后。而你是一个正在异陌的环境里发呆发冷发抖的孤独者,你需要的正是他们拥有的或者准备给你的,于是你情不自禁地伸出手一把抓住了人家伸过来的手,仿佛那便是救命的稻草你再也不会松开了。文化的交融实际上就是人与人的交融,是这一类人和那一类人建立起来的新关系,是在新关系的发展中所呈现的心理认同和心理结构的变化,是你拥有了他的份额他也拥有了你的份额的等价或不等价的交换,是生存的欲求寻找满足的过程,是完全带有世俗色彩的学习、模仿和占有。你的老师是回族,他带给你的就是回族文化;你的同学是维吾尔族,他带给你的就是维吾尔族文化;你的同事是土族,他带给你的就是土族文化;你经常去吃饭的那家饭馆是撒拉族人的饭馆,它带给你的就是撒拉族文化。有一天你恋爱了,恋爱的对象是个藏族小伙子或者是个藏族姑娘,于是你就成了藏族文化的承载者和受益者。文化通过本土的居民直接或间接地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你所表达的意志、你所遵循的规矩、你所服从的习惯、你所采取的行动,成了你自己。但是你和你的家庭、你的环境都没有特别地强调这一点,如同一个健康的人在一个能够正常呼吸的地方永远意识不到呼吸的重要,自然也就用不着强调空气的存在一样。脉搏的正常跳荡恰恰是你根本就感觉不到的跳荡,肝胃肾脾的正常运动恰恰是你根本就不在意的运动,如果哪一天你感觉到了它们的跳荡、它们的运动,那就说明它们出了问题,说明你有病了。文化正是在你感觉不到的时候,成了你心身两地性命攸关的搏动和决定一生的存在。
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空气在夜晚走动,云彩在天空飘逸,时间在身边流逝,包括你自己,谁也没有抓住什么,或者记住什么。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变了,你在镜子面前看到你跟那么多人不一样了。你极想跟他们一样,但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你再也回不到从前,再也不能跟你那没到过西部的父辈祖辈一样了。这面镜子当然不会镶嵌在你妻子的梳妆台上,而是活动在西部之外的某个地方,活动在许多人的脸上——那么多眼睛诧异地看着你,让你陡然觉得:在西部毫无特色的你,一离开西部就鹤立鸡群了。并不是说你很出色,而是你很特别,你天然另类,不拉不弹也是新声异曲,和那里的人云泥相隔,九天九地。
首先你在放肆地喝酒,喝的是五十五度以上的烈性酒,边喝还要边唱,还要划拳,还要让所有人跟你一起喝,别人不喝你就生气,就说人家看不起你;你用殷切的语言劝酒,用吓人的喊叫劝酒,用动听的歌声劝酒,声言如果别人不喝干了你的敬酒,你就要在他面前一辈子唱下去。你的想法是不把对方灌醉放倒就不足以表达你的诚意,不把自己喝得吐出来就不能证明你是那种舍了老命也要让朋友喝好的朋友。你的声音大得震耳欲聋,让全酒店的人都侧目都惊奇,不知道对你说什么好。这时候你忘了,你的这种做派是从西部的本土居民那里学来的。在西部,你曾经无数次地被人敬酒,无数次地受到划拳的挑战,无数次地在主人的歌声里喝干了杯中的伊犁特或者青稞酒;你曾经不止一次地醉倒在自己的家中或者朋友的客厅,也就是说你不止一次地接受着别人的诚意,也不止一次地用“玉山自倒非人推”的方式告诉别人你绝对是够朋友的。
你还会经常提着礼物到你的部下或者朋友或者同事家里去。就像在西部那样,你希望人家留你在家中吃饭喝酒直到深夜、直到天晓,可是这年头,早就不是“行合趣同,千里相从”了,早就是行不必合,趣不必同,对门不必通了。哪里有在家中请客留人的?人家不留你,你就很失落,就公开地指责人家不够朋友。人家莫名其妙,说:我招你惹你了?再说为什么非要“够朋友”?“够朋友”是什么级别的问题?它能给我带来什么?高升?长级?发财?出国?还是别的运气?
更让你失落的是,你在西部热情似火地接待了广州人赵钱和孙李,可是等你到了广州,拿着当初他们送给你的名片依然热情似火地找到他们想叙旧温故时,赵钱和孙李却不认识你了,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想起来了也是白搭,人家别说是跟你一起吃饭喝酒到天亮了,就连跟你说十分钟话的工夫都没有。你在失落的同时又很生气,又说人家不够朋友不讲义气,几乎是骂骂咧咧的。认识赵钱和孙李的周吴和郑王告诉你:“你这人怎么这样?什么叫够朋友?够朋友就是不给人家找麻烦不浪费人家的时间,这在我们这里很正常。我问你,你们西部人的时间是拿什么来计算的?”你回答说:“我们西部人的时间是拿钟表来计算的,难道你们的不是?”周吴和郑王说:“对,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时间都是用金钱来计算的,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就看他的一分钟值几个钱。你刚从落后地区来,还不懂,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你这才明白过来:人家根本就不可能像你接待人家一样接待你,因为你从落后地区来,你有大量的时间用于培育人情和礼貌而人家没有。人家处在汹涌的挣钱潮流里身不由己,哪管什么“居则同乐,死则同哀”的朋友之谊,哪管什么“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的莫逆之交。这时候你表现出了一个西部人对放纵情绪的爱好,那就是伤感,你哭了。你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想到你有那么多情深意长的朋友,但是他们都不在你身边,都在遥远的西部,你哭了。你是个热情惯了、真诚惯了、心血来潮惯了的人,你不习惯如此凉薄、如此轻浅、如此容易被忽视的人情。你晶莹的眼泪带着西部从你眼前消失后的迷茫,带着“西部情感”温暖而凛然的傲气,带着“西部文化”不甘寂寞但又不得不寂寞的孤独。你似乎是有意让你身边的人看到了你的眼泪,你知道他们非常不理解,于是你就使劲告诉人家你在西部的生活:你跟库尔班大叔是唇齿相依的,你跟阿不都老哥是一体同心的,你跟索南爱国一家是融融泄泄的,你跟穆罕默德·阿麦德是情趣相投的。你说的是生活中的故事和人物,体现的却是你的习惯心理和你对事物的固有态度。故事和人物、心理和态度、主体和客体,它们加到一起,就形成了你的特殊的文化背景。你之所以被当地人不理解甚至看不惯,就是因为你拥有的文化背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西部的自然是严酷的,但由此产生的文化却充满了人情的醇厚和炉火般的温馨。它是画布上的暖调子,是音乐里的小夜曲,让你常常沉浸在一种黑夜不黑、寒冬不寒的幸福感觉里,尽管这种感觉并没有带给你什么实际的好处比如增加你的财富积累等,反而让你额外付出了许多。
是的,西部人是不大善于积累财富的。当报纸大张旗鼓地怂恿花钱刺激消费的时候,你很吃惊这样的问题居然也要说得如此郑重,你甚至都不相信真的会有人藏着钱不愿意享受。因为你早就认为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吃掉碗里的肉,而不要考虑锅里还有什么。眼前的清汤永远比日后的干饭重要得多。但是你并不知道,这是高寒带的人普遍具有的一种生活态度,是西部文化对灾难频仍、浮生苦短的一种潜意识的反抗抑或是遮掩。“文化大革命”中,西宁市礼让街揪斗致残过一位老人,就因为他跟别人说:“别相信这主义那主义,明日的富贵根本不如眼前的一杯酒。”也是在“文革”中,有一天我们班主任老师突然莫名其妙地对全班学生说:“你们要记住鸠山对李玉和说过的话——‘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第二天他就不给我们上课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几年后想起来,才意识到这是老师的临别赠言——他在走前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一句话留给了他的学生。1997年夏天,青海人马海福要去海拔近五千米的西藏那曲开饭馆,他的老师劝他不要去,说:“还是古人觉悟高,早就说了,‘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何至辛苦乃尔’。”西部人对这一类语言的着迷可以追溯到古代。汉朝的苏武出使西域,被匈奴扣留,匈奴首领单于派已经投降的李陵说服苏武背汉,其中的说辞便是:“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边地的苦寒、人寿的短暂造就了人们不夸耀既往也不迷信将来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帮助他们在结构自己的人生大厦时,把最敞亮的殿堂献给了今天,就像十多年前我在我的《游牧诗》中所歌咏的那样:“今天,我们活着,完成了一生的快乐。”你活着,而且很快乐,西部就是这样,它会鼓励你有一分钱买一分快乐,有一毛钱买十分快乐,甚至没有钱你也能找到快乐。
当然不仅仅是快乐,还有松弛和散淡,你在牧区生活,你就必然是松弛和散淡的。平常的日子里,慢悠悠的不会有什么变化的生活淡化着你的时间观念,让你在舒缓的节奏里做事或者不做事,那是一种可以让你健康长寿的舒缓,是心理上没有任何负担的舒缓,是无为而治的舒缓。没有什么地方比在草原上更能体现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了。比如说你想工作,那就得先去帐房里跟牧民一起吃饭,吃饭就是工作;你要深入群众,那就必须时不时地去草原上喝酒,而且得喝醉,喝醉了牧民才能把你当自家人,也才能听你的话同时也跟你说自己的心里话。如果你是一个大学生,刚刚分配到县上,县长就会说:“你去森多乡把今年的牲畜存栏数了解一下,我等你晚上回来汇报。”你去了,天黑以前回来了,这时候要是你醉着,你胡话连篇,什么牲畜存栏数早就说不清楚了,县长就会说:“好,是个人才,第一次下乡就能和牧民群众打成一片。”要是你没醉,或者根本就没有喝酒,只是带回来了准确登记着牲畜存栏数的表格,县长就会给组织部长说:“要这样的人做啥哩?一点都不会工作嘛。”当然县长绝对不会辞退你,他会身体力行地带你下乡教你工作。你很辛苦,光骑马走路,从这个帐圈到那个帐圈,或者从这个定居点到那个定居点,就觉得两腿内侧如焚如剐,屁股疼得简直不想要屁股。但是你并不在乎,你知道过上一两年,等磨出老茧来就好了。况且你看到牧民们不知要比你辛苦多少倍,他们放牧、背水、拾牛粪,还要磨青稞、打酸奶、纺毛线,可他们见了别人总是乐呵呵的,这让你觉得他们满脸的皱纹是笑出来的而不是苦出来的。
就这样,你天天在草原上跟牧人打交道,久而久之,你变了,你的性格中有了牧人的乐观,还有了他们的天真,有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掖着藏着的牧人般的直爽,有了化解孤独和苦难的诙谐,有了友善而聪明的幽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你很快习惯了牧家的饮食,天天都是牛腿羊肋巴,顿顿不离奶茶奶疙瘩。这种完全西部化的饮食渐渐改变了你天生的绵软和柔顺,你连自己也没想到地雄风鼓荡起来,阳刚气盛起来,眉眼中明显有了顾色之盼,身体内的青春之潮发愤地奔放着,说起话来更是大声大气,直言无隐,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一个男子汉要求自己的,首先是得到爱情,是对女人十倍的缱绻、百般的缠绵。你做到了。
还有,你愚忠朋友,你死顾亲情,你轻财重义,你知足达观,你嫉恶如仇,你恩怨分明,你处世随便,你生活简单,你热爱自然,你喜欢动物,你尤其喜欢骑马打枪——对你来说,最过瘾的运动就是像马背上的民族教给你的那样,骑着马端着枪,在孤烟正直、落日正圆的荒原上,奔驰啊奔驰,突然看到(也许是假装看到)有动物从地平线上跑来,一枪,两枪,三枪,子弹打光了,什么也没打着。但是你很高兴,因为谁都知道不是你枪法不好,而是你不忍心打死动物,再说许多动物是不能打的,打了犯法,你害怕犯法,西部人都跟你一样格外害怕犯法,他们看上去外表粗犷、举止不恭、无所顾及甚至放浪形骸,但实际上他们很规矩,他们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希望自己离法律远一点,最好永远互相不认识。
六
西部是远大的,远大得让人不知道如何形容,通常的形容词譬如寥廓、空广、苍莽、无际、辽远、十万八千里等都显得不够分量而流于浅薄,那就不形容了吧,就说它大。一个“大”字能解决的问题,我就没有必要再纠缠了,需要纠缠的倒是:大地面上必然会出现的多种人,是如何以不同的情态气势营造了一个一直被外界忽视着的庞大的“西部人”(“西部人”在这里指的主要是西部的移民亦即汉族人,下同)的群体,是如何在这个群体内部以各自为阵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完成了对“西部人”这个大概念的塑造。对于这种塑造,虽然我们可以使用人类学中“用于一切的公设”来进行涵盖和总结,但我本人对这种无趣而抽象的“公设”毫无兴致,我宁可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也不希望所谓的“同一类型”来打搅我。可以说正是因为我看到大地面上如此众多的“西部人”是各色各样各具风韵的,才使我有了观察的好奇、追问的兴趣和描述的冲动。
就拿青藏高原来说,青海和西藏两个省区的“西部人”有着太明显的区别。西藏的“西部人”较之青海要少得多,可谓是少而精,少而能的,居留的时间也比较短,大致只有半个世纪。也就是说,西藏的“西部人”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进入西藏的,截止七十年代末,陆续有一些干部、军人、知识青年前往拉萨、日喀则、那曲等地以及各个边关要隘安家落户;八十年代至今,去的大多是生意人、援藏干部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和打工者。就整体而言,他们有自强不息的素质,有“冬宜冰藏夏宜水显”的适应能力,有能够给他们自己带来信心的聪明才智,甚至有一些是艺术感觉极佳、创作能力极强的顶尖人才,虽然未见得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作品,但却以使命般的执着完成了西藏艺术全国化、宗教艺术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倾情而为,卓尔不群地挥洒着自己那被藏土的神圣和人群的秘密呼唤起来的天分和激动,架起了一座西藏和内地、西藏和世界灵灵相通的神秘桥梁,强烈的西藏宗教和世俗的艺术岚光因此而广播于西藏之外的许多地方。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没有把艺术气质窃为己有,而是无意中均匀地分摊在了每一个“西部人”身上,让外界的人一接触到他们(不管是干部、军人还是生意人、打工者)就会有一种接近艺术的感觉。由于对藏传佛教的耳濡目染和对西藏生活的身体力验,他们的人生境界和处世态度常有与众不同之处,对事物也有着较为明澈和较为圆润的看法,显得激而不躁,愤而不争,独而不孤,感而不伤;浪漫而又能吃苦,理想而又能务实,标新而又能守成,放达而又能持重。他们经常处在一个无所管束的环境里,却又能自己寻找规矩,进退中度,从不像西部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容易自我放逐。由于西藏是全国全世界都关注的地方,他们干出一点名堂就格外受人注目,所以他们一方面是建设西藏,一方面是享受西藏,可谓得天独厚。
无庸置疑,西藏的“西部人”和别处的“西部人”一样也生活在一个地处边远、环境艰苦、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但却没有别处的“西部人”那种令人着急的自馁自卑,因为他们有西藏作为安身立命的资本,有西藏在世界上的声誉作为强有力的支撑。西藏被认为是人类的最后一块净土,尽管“净土”这个概念早已变得不知所云,原始的没有尘世污染的“净土”含义和正在走向物质繁荣的西藏相比,也早已判若霄壤,但他们仍然乐于把“净土”挂在嘴上,以显示自己是一个被“净土”净化过的西藏人。因为相对于工业文明高度发达同时又有灵魂污浊、铜臭泛滥、道德沦丧等负作用的外界来说,理想中的“净土”自然具有朦胧而强大的诱惑。西藏是“西部人”巨大的精神财富,是任何发达和繁荣都换不来的本钱或者说是光耀。一个人到了外地,说他是从西藏来的,马上就不一样了,人家看他的眼光就像看喜马拉雅山一样带着一种远距离的景仰。正是这种景仰的存在,使西藏的“西部人”有了良好的自我感觉,有了超越西部的最大可能——事业如此,意识如此,行动也是如此。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西藏的“西部人”虽然更加遥远地离开了内地,但却和内地保持着与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区的“西部人”根本就无法企及的关系。这种关系有赖于外界对西藏的关注,有赖于他们的“人气”,有赖于他们和内地故乡的联系,也有赖于他们对虽然不发达却也不闭塞的交通的选择。
西藏和青海同属于一个地理板块即青藏高原或者叫世界屋脊,那条被称为“天路”的两千公里长的青藏公路把两个省区牢牢地连在了一起。但西藏的“西部人”并不喜欢通过依然遥远的青海走向内地,他们通常会选择从拉萨到成都的空中通道或者川藏公路,尽管川藏公路常常因塌方、山洪、泥石流等灾难而无法畅通。也就是说,他们和四川以及成都的关系要比和青海以及西宁的关系密切得多。这里面的原因,除了做生意和来打工的大多是四川人之外,除了从拉萨飞往成都要比从拉萨飞往西宁容易得多之外,除了西藏和四川在我国原有的行政区划上同属于大西南之外,更重要的是,四川以及成都的经济和文化之繁荣远远不是青海以及西宁所能够望其项背的。到了成都,就有大都市的感觉,尽管它仍然属于西部,但它和内地的大城市比起来又能差到哪里去呢?而西宁就不同了,你花几天几夜的时间千里迢迢从拉萨来到这里,发现你到达的仍然是一个远离内地的边疆城市,虽然它离真正的边疆早就是几千甚至上万公里了。
还需要说到的是,西藏的“西部人”虽然对西藏一见钟情,并且会终身相爱,但扎根不走的却很少,毕竟年龄不饶人,毕竟高寒缺氧的气候和他们那内地育成的身体并不是一对铁心牵手、矢志不移的伴侣。更重要的是,虽然他们对自己是一个西藏人深信不疑,虽然他们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在西藏度过,但西藏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梦,一个没有做完的梦;仍然是一片永远都无法企及的雪峰极顶的圣殿,一个从来都没有真正触摸过的自然和宗教的理想部洲;仍然是一个传说,一个藏着太阳孕育着无边光明的神性的高地山群。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一个一直憧憬着西藏却一次也没去过西藏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没有和本土的居民血脉相通的经历,没有几代人和雪域高原耳鬓厮磨、如胶似漆乃至患难与共、生死相托的关系,没有把自己祖辈父辈的身躯交给天葬场的鹫鹰,没有把自己的精神交给山巅上猎猎飘扬的经幡,没有把儿女的生命交给神人神山神畜的信念,任何一个“西部人”,对需要献上灵魂的西藏来说,都只是一个客人。
而同样有大量“西部人”群落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就完全不同了,首先这些省区的“西部人”都有悠久的移民历史,几代、几十代都过去了,“西部人”和土地的融洽早已是天机云锦,妙合自然。最初的移民对环境被动性的适应几百年前就变成了“一方土地养一方人”的良性循环——这样的山水只能出产这样的物,这样的地貌只能育成这样的人。尽管近五十多年中,由于国家多次实行戍边屯田、遣犯垦荒、兴办实业、支援边疆、上山下乡的政策,不断有新移民潮水般涌来,但并没有改变已然形成的移民和环境浑然合一的局面。铁打的营盘一样不动不摇的老“西部人”,以最大的包容性和新移民你七我八地混同起来,让后者迅速完成了人格西部化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个过程的完成,才使我们透过各地判然有别的自然水土和人文水土,看到了一个关于“西部人”的虽然残缺但大致还能意会的轮廓,也看到了轮廓之中组成部分的千姿百态和我们暂时还不能抹去的个性色彩。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本站只支持手机浏览器访问,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
小说推荐:《真灵九转》【新键盘小说网】《蝉动》《诡秘之主》【天空小说网】【异度荒尘小说网】《炼道升仙》《要高考了,机甲到底怎么开啊》《斗罗:七杀惊绝世》《全职高手之我有一个背后灵》
天才一秒记住【格林文学】地址:glxsw.cc,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